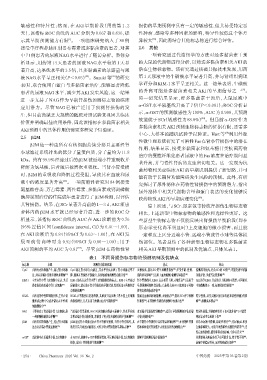Page 136 - 《中国药房》2025年2期
P. 136
敏感性和特异性;然而,在 AKI 早期阶段(用药第 1、2 损伤的早期预测中具有一定的敏感性,但其易受特定恶
天),该指标 ROC 曲线的 AUC 分别为 0.667 和 0.636,提 性肿瘤、感染等多种因素的影响,特异性较低且个体差
[36]
[7]
示其早期预测能力有限 。一项临床研究纳入了 88 例 异较大 ,因此需结合其他标志物进行综合评估。
接受单疗程静脉注射妥布霉素或多黏菌素的患者,对其 2.6 其他
中71例患者的尿液NAG水平进行了随访分析。整体分 一项研究通过代谢组学的方法对经多黏菌素干预
析显示,用药第 14 天患者的尿液 NAG 水平较第 1 天显 的大鼠的代谢物进行分析,以筛选多黏菌素相关AKI的
著升高,达基线水平的3.5倍,且多黏菌素的暴露量与尿 潜在生物标志物。该研究通过核磁共振技术发现,用药
[33]
[34]
液 NAG 水平呈正相关(P<0.05) 。Suzuki 等 的研究 第1天尿液中的牛磺酸水平显著升高,并与肾组织病理
表明,联合使用白蛋白与多黏菌素治疗,能够显著降低 学评分和KIM-1水平呈正相关。这一结果表明,牛磺酸
[37]
患者的尿液NAG水平,减少其AKI发生风险,这一结果 的升高可能是多黏菌素相关 AKI 的早期信号之一 。
进一步支持了NAG作为早期肾损伤预测标志物的临床 另一研究结果显示,经多黏菌素干预后,大鼠尿液中
α-GST 水平较基线升高了 7 倍(P<0.001);ROC 分析显
应用潜力。尽管 NAG 已被广泛用于预测肾损伤的发
示,α-GST的预测敏感性为100%,AUC为0.998,其预测
生,但目前尚缺乏大规模的随机对照试验来巩固其临床
[38]
效能优于 SCr(敏感性为 88.8%) 。但目前 α-GST 作为
价值并明确最佳应用条件,因此该指标在多黏菌素相关
多黏菌素相关AKI预测生物标志物的证据有限,还需多
AKI预测中的具体作用仍需更多研究予以验证。
[39]
中心、大样本的随机试验予以验证。Hart 等 利用外源
2.5 β2M
性微生理系统研究了可溶性Fas在肾小管损伤中的潜在
β2M 是一种由所有有核细胞持续分泌且主要经肾
作用,结果显示,接受多黏菌素和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
小球滤过系统排出的低分子量蛋白质,分子量约为11.8
治疗的囊性纤维化患者尿液中的Fas浓度在治疗期间显
kDa。约有99.9%经滤过后的β2M被近端小管重吸收并
著升高,并与慢性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。这一发现为抗
降解为氨基酸,后者随后被再次重吸收。当肾小管受损
菌药物相关亚临床AKI的早期识别提供了新思路,并可
时,β2M 的重吸收和降解过程受阻,导致其在血液和尿
能有助于长期肾功能障碍发生风险的预测。此外,有研
[35]
液中的浓度显著升高 。一项前瞻性研究对 84 例接受
究探讨了尿外泌体在药物性肾损伤中的预测潜力,指出
氨基糖苷类、万古霉素、两性霉素、多黏菌素或钙调磷酸 尿外泌体中相关代谢物含量和蛋白表达的变化能够反
酶抑制剂治疗的住院成年患者进行了β2M检测,以评估 映药物致AKI的早期病理变化 。
[40]
其肾损伤。结果,在SCr显著升高前的1~3 d,AKI组患 综上所述,与SCr、尿素氮等传统肾损伤生物标志物
者体内的 β2M 水平就已经显著升高;进一步的 ROC 分 相比,上述新型生物标志物的敏感性和选择性更好。这
析显示,该指标 ROC 曲线的 AUC 在 AKI 诊断前为 0.76 些新型生物标志物不仅能反映出肾损伤早期阶段(即在
[95% 置信区间(confidence interval,CI)为 0.41~1.00], 形态学变化尚不明显时)上皮细胞的微小损害,而且能
在 AKI 诊断后为 0.84(95%CI 为 0.63~1.00),在 AKI 发 一定程度上区分近端小管、远端小管或肾小球等具体损
展至病情高峰时为 0.92(95%CI 为 0.80~1.00);用于 伤部位。笔者总结了各种新型生物标志物在多黏菌素
AKI 预测的平均 AUC 为 0.81 。尽管 β2M 在药物性肾 相关AKI早期预测中的机制及优缺点,具体见表1。
[23]
表1 不同肾损伤标志物的预测机制及优缺点
标志物 来源 预测肾功能的机制 优点 缺点
CysC 由所有有核细胞产生,通过肾小球滤 CysC通过肾小球自由滤过,其水平升高反映了肾小球滤过率下 灵敏度高,能比SCr更早预测肾损伤 ;不受年龄、性别、 检测成本较高,约为SCr的10倍 ;可能受到甲状腺
[13]
[17]
[13]
过,并在近端小管被重吸收和降解 [13] 降,能够在肾损伤早期检出,以较敏感地预测肾功能异常 [14] 肌肉质量影响 ;适用于血清检测,检测结果稳定 [16] 功能异常、炎症等因素影响 [18]
[21]
KIM-1 主要在肾小管上皮细胞中表达,尤其 KIM-1的高表达是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的标志。KIM-1主要通过 肾小管损伤时,KIM-1表达显著上调,灵敏度高 ;适用于 AKI诱导KIM-1升高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楚;不同研究
是在损伤的近端小管上皮细胞 [19] 尿液排出,能有助于肾小管损伤的早期识别,特别适用于药物性肾 早期预测药物性肾损伤;已获得美国FDA批准用于药物 中的截断值不一致,标准化程度较低 [19]
毒性的检测 [19] 性肾毒性的临床评估 [22]
NGAL 由活化的中性粒细胞分泌,主要在骨 NGAL在肾损伤后迅速释放,其浓度升高反映了肾小管上皮细胞 能通过血液和尿液检测,灵敏度高 ;能比SCr更早预测 特异性低,易受其他因素(如炎症和恶性肿瘤)的影
[26]
[29]
髓形成过程中合成并储存在中性粒 的损伤程度,尤其适用于预测AKI的早期阶段 [26] 肾损伤 ;在药物性肾损伤的预测中表现出色 [27] 响 ;检测成本较高 [12]
[26]
细胞颗粒中 [25]
[32]
NAG 主要存在于肾近端小管上皮细胞,是 当近端小管受损时,NAG可从细胞内释放至尿液中,其水平升高 对近端小管损伤特别敏感 ;适用于早期预测和评估近端 特异性较低,其他病理条件下也可能升高 ;可能受
[31]
一种溶酶体刷状边界酶 [31] 表明近端小管功能受损,常被用于肾小管功能障碍的早期预测 [31] 小管功能障碍 [33] 到尿素或重金属的干扰 [32]
[23]
β2M 由所有有核细胞产生,经过肾小球滤 β2M通过肾小球滤过后在肾小管被重吸收,当肾小管受损时,其 在早期肾小管损伤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;在药物性肾损 容易在尿液中降解,稳定性较差 ;受尿液pH和蛋
[36]
过后在近端小管被重吸收 [35] 浓度升高并通过尿液排出,可作为肾小管损伤的早期标志物 [36] 伤和移植相关肾损伤中表现出良好的预测能力 [36] 白酶影响较大,可能导致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 ;受
[35]
特定恶性肿瘤、感染等因素的影响,个体差异大 [36]
[42]
α-GST 高度集中在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中 在AKI时,尿液中α-GST排泄量增加,可反映近端小管上皮细胞的 能够早期预测近端小管损伤 [41] 非肾脏相关疾病条件下也可能升高,特异性不强 ;
损伤,适用于肾损伤的早期预测 [41] 尿液中的稳定性差,需要特殊储存条件 [43]
· 254 · China Pharmacy 2025 Vol. 36 No. 2 中国药房 2025年第36卷第2期